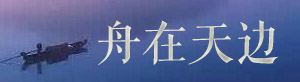岸上屹立着一座朴素的寺庙——赤岸庙,它的尖顶远望像一把长剑凌驾于绿树梢头,守护村庄的宁静。每当做法事的时候,僧众结队巡逡,飘逸的袈裟映红了半个湖面,这些快乐的鱼就在这片红色的水里和岸上苍凉的唱喏里游动。这时候人们便向湖里张望,期望发现红纱帐——在红光里游动的大队鱼群——据说它们是村庄的灵魂。如果发现了红纱帐,岸上的队伍会停下来——烧香、鸣炮——看着鱼群游走。
村庄三面环水,湖畔、山岗零星散落一些形状各异的田地,像点缀其间的水塘一样,它们都有自己的名字,或根据所有者的名号、或是根据田地的形状来命名,如水生田、连耳田……十五六岁以上的村人头脑里有一幅活的地形地貌图,他们在道场纳凉或在堂屋烤火闲聊时,说哪一寸田地都心中有数,绝对不需要多费口舌。
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船,但并不靠打鱼为生。全村人都沾亲带故,没有儿子的老人会有亲族将自己最大的儿子过继给他,直至老人入土安息,在坟前立块石碑刻上子某某立。亲戚们住得都不远,他们来了,主人不慌不忙到湖里撒上一网,就像到菜园里拔一颗葱一样简单。
我就是这个村庄的孩子。祖上原本住在江西乐安,为避水患,顺流而下迁徙至此,依然择水而居,依然为人师表,培育的异姓弟子中榜、做官,本族后辈却总“名落孙山”。我的曾祖道池老人沉不住气了,那个炎热的正午,他来回几趟,把所有的书籍堆到道场正中,颤巍巍将它们点燃,奇异的书香弥漫村庄,老人展开双臂、仰天恸哭而长号:“孙氏永绝书香!”尔后,面无表情地走出了村庄,再也没有回来,留给村庄的,只有那白发苍然的背影。家族受到了诅咒,没有人找理由责怪曾祖父,仿佛老人为后辈的不思进取和落榜提供了最佳理由。
村庄依然宁静。村庄的童年像鱼一样简单而快乐,一年里都能看到好几回红纱帐。然而好景不长,当一个完整的村庄被分成几个生产队时,田地失去了它们原来的名字,除了几分地的菜园,全部由集体耕种;村头的寺庙被砸毁,残垣断壁杂草丛生;不准私自下湖捕鱼,所有的船都在沙滩上倒卧着,逢年过节,生产队派人下湖捕鱼,按人口分发各家。红纱帐不见了!
红纱帐不见了,人们暗自纳闷:鱼群哪里去了呢?一个失去灵魂的村庄在贫困线上挣扎,甚至新一轮“大包干”后的许多年也是如此。村庄宽容了那个带头砸寺庙的“队长”,他也是村庄自己的子孙。“这块地脉,死了!”我和一些兄弟走出了村庄。
久别还乡,我意外地发现村子东头重建的赤岸庙,门联是“仁山遥指,智水环流”。秀劲的颜体,是我故去不久的兄长的手笔。大年初一,人们敲锣打鼓在寺庙集会,结队游行湖边。
我想:红纱帐也许很快就会回来。
(雁洲)